為什麼說,上海城市的煙火氣,看咖啡就知道?

第二屆上海咖啡文化周拉開帷幕,百余項活動精彩紛呈。
有人說,咖啡與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溫情氣韻,具有內在的“互文”關系。
城市的煙火氣,看大街小巷的咖啡就知道。
一個豆子跨越時空的旅程
盛夏蟬鳴,穿過玻璃窗外的梧桐枝葉。手中的咖啡,佐以街角熟悉的風情,剎那便能感知——如常的上海,在咖啡的香氣中醒來了。
咖啡,成為上海重新煥發活力的公認指標。
今天的上海人,清晨的咖啡是一天的開始,下午的咖啡是再度飽滿工作的信號。
一起喝咖啡,或許是推進工作或碰撞靈感的形式,也或許是人與人之間私密的心靈交往。

從文化角度看,推開哪一家咖啡館的門扉﹔點的是特調、美式、奶咖還是瑰夏手沖﹔把咖啡作為必需的提神飲品、社交流量、裝扮符號,還是富有儀式感的手作體驗……不同選擇的背后,是每個人對生活、文化與身份認同的理解。
從產業角度看,一旦喝了一杯咖啡,就卷入了一場遍及世界的經濟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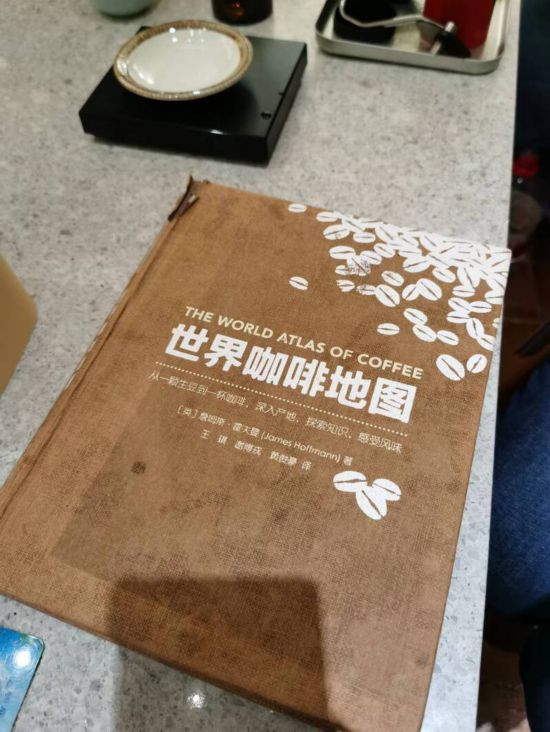
小小的咖啡豆,從赤道的另一邊經過生產、加工,跋涉千裡,最終被全世界的人群大量消費。
當今世界,隻有油料超過了咖啡的交易量。每一杯咖啡的背后,可能都是一場產業馬拉鬆,與千裡之外的全球交流息息相關。
思想家吉登斯曾在《社會學》一書的前言裡提示,“喝咖啡”這個看似簡單的行為,包含著復雜的內涵。當它融為日常活動的一部分時,它是一種象征和儀式,也是一種習俗和文化。
不過別誤會,它並不隻屬於西方文化。關於咖啡起源的一個版本是,大約在公元6世紀,咖啡豆的秘密被阿拉伯牧羊人發現。它先傳到也門與摩卡,幾度被禁止交易,又被推廣擴大種植面積。它一度被稱為“阿拉伯之酒”。
1600年代,咖啡與歐洲擦出激烈的火花,人們在咖啡館裡對話、思考,讓它成為思想交流與社交的中心。咖啡與美洲相遇,則塑造了一張商業化、產業化的現代版圖,誕生了各類商業標准化。
1844年,咖啡來到開埠不久的上海。從此,田漢、林徽因等文化名人都寫過與咖啡相關的作品。
從上世紀初到今天的影視劇中,喝咖啡的場景,依然是大家對上海城市面貌的標志性想象。
當咖啡來到這裡,一場更大的跨界與融合創新,正等著它。
源頭品控,力求掌握在自己手裡
2012年的上海,現磨咖啡市場初露端倪。
作為國際各類咖啡專業証書考試的考官,陳嘉峻遇到一名上海學員,對方打算在上海開一家烘豆工廠,因為“這裡還是一片亟待開墾的沃土”。
彼時的上海,咖啡館多了、品種豐富了、資本進來了,然而產業鏈的更前端,如咖啡設備、烘豆技術等環節依然稀缺,咖啡生豆的品種也很少,大部分人隻知道藍山。
這就顯出培訓和資格考試的迫切性。
陳嘉峻決定定期來上海從事認証培訓業務。他的課程一般12人左右規模,持續約9天,費用上萬元。有精品咖啡操作類考試,有咖啡豆烘焙類考試,也有杯測品鑒類考試。
近幾年,學員來源越發“多元”,有的來自咖啡行業,也有些是完全不相干的普通愛好者,如律師、建筑師、攝影師等,他們出於個人喜愛,願意花錢進行系統而專業的學習。

普通人的熱愛,或許能真實反映咖啡在上海城市生活的分量。而當年開烘豆工廠的學員告訴他,2021年,沒怎麼努力,烘豆工廠的盈利就增長了50%。
如今上海大街小巷星羅棋布的咖啡館已經成為城市的一道風景。而數量的背后,其實是更復雜的產業鏈在支撐。
一杯咖啡的品質,70%靠豆子。
好的咖啡豆從哪裡來?生豆就像生牛肉,基因很重要,而大廚的烹飪水平也很重要,兩者直接影響了端上桌的牛排,究竟賣幾十塊,還是上百元。
從源頭看,巴西是全球產量較大的咖啡豆產區,其豆子風味平衡,性價比不錯。而非洲的咖啡豆以高品質聞名,風味鮮明、品種多樣。埃塞俄比亞還有一些古老的“原生種”,未經人工雜交,豆子風味強烈。
中國也有自己的咖啡豆產區,如雲南。
過去,雲南的種植管理比較粗放,處於市場的底端,大多被咖啡館用作拼配豆。其中一個雜交品種“卡蒂姆”,抗病能力強,但離精品咖啡級別有很大差距,一度被專業人士嘲諷說,它帶著一種“魔鬼的尾韻”。

雲南,一杯咖啡裡的鄉村巨變。新華社發
2018年左右,上海咖啡館進入高速增長期,一家家精品咖啡店此起彼伏。有沒有優質的國產精品咖啡豆冒泡,而非全部依賴進口?新的需求,催生出一批行業年輕人深入雲南。
他們尋找海拔更高的咖啡產地,帶去了精品咖啡的培育方法,提升咖啡庄園的精細化管理水平。除水洗、日晒外,還迅速推廣了厭氧、酒處理等時髦手法。

電影《一點就到家》就表達了中國咖啡人對雲南的向往。
雲南咖啡豆從“這能喝嗎”變成“讓人驚喜”。2018年,它走出國門,參加了SCA(全球精品咖啡協會)精品咖啡展會。自此,雲南咖啡豆能以精品豆的身份,出現在上海的精品咖啡店。
而烘豆,就好比大廚的烹飪環節,是制約咖啡豆品質的另一個瓶頸。
2014年左右,幾個國產烘豆廠牌逐漸崛起,打破了國外精品咖啡豆長期以來的壟斷地位。如今,不僅僅是國產烘豆工廠,上海一批咖啡店店主,甚至是個體愛好者,已經開始自己烘豆自己賣。
就在幾天前,《上海市焙炒咖啡開放式生產許可審查細則》發布,意味著無須獨立房間或專業工廠,符合條件的咖啡館均可一邊售賣咖啡,一邊向消費者展示焙炒咖啡豆的生產過程。
隻有當生產過程與消費終端共同繁榮,當我們自己能生產原材料時,上海的咖啡市場才真正有了產業積累。
咖啡在這座城市,真的成為文化生長與創造的一部分,也是參與世界產業鏈、與全球對話的一部分。
本土化創新,萬物皆可“咖啡+”
每年一次,在上海舉辦的國際酒店及餐飲業博覽會(簡稱Hotelex),已經成為中國咖啡從業者交流的盛宴。
也是在這個展會上,一些行業前沿被更多人看到,逐漸成為上海咖啡的現象級爆款。
比如冰博克,它起源於一次咖啡大賽。一名選手突發奇想,用歐洲人釀酒的方法來提純牛奶,取名為“冰博克”(Eisbock,德語)。卻沒想到,這個小眾技術在上海展會上得到迅速推廣。如今,冰博克奶咖已成為流行基本款。

在上海,咖啡是多變的、好玩的、跨界的,萬物皆能“咖啡+”。
它可以與江南水鄉的美食融合,紅豆、薏仁、綠豆、紅棗、血糯米、米酒等被調入咖啡,創造了豐富的口味。
它也與本土的茶文化彼此心心相印。
幾年前,Hotelex展會上,有人用虹吸壺煮茶、煮泡面,令參觀者倍感震驚。然而沒過多久,中國大街小巷的茶飲店裡,開始用冰滴、冷萃、冷泡等咖啡萃取手法提煉花果茶。

反過來,中國的綠茶、花果茶,又給咖啡注入了新的靈感。
奶茶店不斷制造“爆款”的模式,也被上海的咖啡品牌學去了。如近幾年火爆的“生椰拿鐵”,炎炎夏日頗受歡迎的“青檸”系列等。
想知道今年中國市場流行什麼咖啡?來上海逛一逛。
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咖啡可以加風味糖漿、加奶油、加冰沙、加堅果,甚至加椰子水、加桂花、加龍井茶葉、加荔枝、加水蜜桃、加仙草、加龜苓膏……對中國消費者來說,咖啡既可以是提神的專業飲品,也可以是“帶有咖啡元素的復合飲料”。

這樣的現象,其實在歐美城市十分少見。一位消費者表示:“星巴克在西方城市相對簡單,有些小店的品類隻有上海的三分之一。”西方人把咖啡當作日常飲料,品類幾乎十幾年不變,以幾個基本款為主。
能將咖啡玩得花樣百出、奪人眼球,是這邊獨有的創新。
國際品牌進入上海市場,也會隨之調整自身的設計。
手沖咖啡領域,以玻璃制品起家的日本百年老店HARIO一直是行業標杆,其雲朵壺、V60濾杯,被捧為手沖咖啡器皿中的經典款。2010年,品牌來到上海開設海外分公司,在這裡的文化碰撞,激發了新的設計思路。

比如HARIO經典的虹吸壺,新版本為茶葉愛好者提供了除絨布濾網之外的不鏽鋼濾網。
發現國內手沖咖啡愛好者更多喜歡單人品玩,而非家庭分享,品牌商推出了一人份濾杯套裝+中小號手沖壺。

為了適應國人喜愛喝熱水的習慣,品牌商又推出了帶手柄的玻璃壺、冷水壺、水杯等。
這兩年,精致露營享受大自然成為城市的網紅玩法,HARIO也緊隨潮流,推出了OUTDOOR系列器皿,比如硅膠材質的V60濾杯,平鋪后就像一張小紙片,便於攜帶。
中國市場也催生了獨有的咖啡創新類型:便攜式咖啡液。
十多年前,本是平面設計專業的鐵皮(網名),因熱愛咖啡,來上海的精品咖啡公司工作。彼時,人們想要喝上一杯芳香四溢的現磨咖啡並不容易,除了少數發燒友,普通人隻能去店裡購買。
有沒有一種可能,把現磨咖啡的風味保留下來,做成濃縮咖啡液隨身攜帶,讓咖啡也能“裝進口袋”?
2014年,鐵皮在上海創立了自己的咖啡品牌永璞,主打產品正是小巧如膠囊的咖啡液。
西方也發明了膠囊咖啡,不過必須使用膠囊咖啡機進行萃取,而永璞的咖啡膠囊打開后,直接把咖啡液倒入礦泉水稀釋即可,人們隨時隨地,想喝就能喝。這可能是國內第一個使用閃萃技術的常溫咖啡液。

如今,跨業態發展成為上海咖啡市場的一大特色。
比如便利店咖啡,全家、羅森、光明等紛紛入局。上海美食的老字號喬家柵、邵萬生開起了精品咖啡館。更別說郵政企業、石油企業也在上海嘗試咖啡店。

各種“咖啡+”在城市街頭琳琅滿目,如書店、音樂廳、酒店、聯合辦公、健身房、服裝店,都與咖啡融合,打造復合的文化場景與城市空間。而潮流品牌、一線品牌還會向咖啡品牌拋出“橄欖枝”,推出聯名活動、文創產品。
在上海,咖啡花樣之繁多、場景之多元,給未來的創新以無限想象。
咖啡人的城市心路
6月1日10點,解封第一天,南昌路的OZ咖啡館開門了。“好久不見”“想念你家的咖啡”,鄰居們紛紛涌入。店主陳穎和他們一一打招呼。
南昌路是上海精品咖啡最集中的小馬路之一,短短幾百米長,一度雲集了50多家各具風情的咖啡店。在黃浦區瑞金二路街道的支持下,南昌路成立了“金咖聯盟”,希望未來咖啡店集體合力,打造這條小馬路的文化腔調。


這一天,OZ咖啡館來了約1000個客人,40%都是老面孔。后來,因疫情反復,不能堂食,客人們就在窗口買一杯咖啡帶走。
陳穎經歷了一段焦慮時光,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她把主業賺到的錢貼補這間咖啡館,停工在家期間,依然給員工發了約5000元的月工資。
“老客戶和員工,是我堅持的動力。”陳穎說。這家咖啡館以周邊回頭客居多,年齡大多40來歲。附近的理發店、烘焙店、文創店,辦公人士、文化創意人士、老居民,已經習慣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客堂間”。
陳穎與記者說話間,一名穿著拖鞋的男士推門而入,向陳穎打了聲招呼,就直奔操作台與員工熟絡地寒暄,仿佛在自己家裡般自由。“他也是我們的老客人,附近居民,有時候一天來串門好幾次。”陳穎解釋。
上海的咖啡館更新迭代很快。疫情也讓她思考許久,如何取舍,開店的初衷是什麼。
當每天,熟面孔們推門而入,說就為了“熟悉的那一口”時,陳穎明白了咖啡店之於自己的意義和動力。
在北京西路與銅仁路的街角,00后店主何維琦正在咖啡館裡忙碌。店裡隻賣雲南咖啡,准確說,隻用店主自家產的咖啡豆。
何維琦在雲南德宏老家擁有4000多畝咖啡園,父母種植咖啡超過20年,過去,家裡直接把生豆賣給中間商。
去年,她選擇在上海開了這間咖啡館,店名就叫德宏Dehome,出品頗有特色。

店裡的飲品中,有的添加自家產的咖啡花的花蜜,有的用咖啡果皮泡茶,有的加入雲南胭脂果增加風味。

不定時還會推出一些雲南特色套餐,比如冷泡咖啡搭配雲南鮮花餅,或者應季的烤鬆茸、雲南火腿等。
為什麼選擇來上海開店?“這裡匯聚了全國業內最優秀的人才,可以開拓眼界。”何維琦說,“另外,檢驗我家豆子好不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來最激烈的市場拼殺。”
去年,何維琦回老家做了一件有儀式感的事情:為自家庄園裡的咖農們制作一杯手沖咖啡。這些咖農從來沒有嘗過咖啡,“好苦呀”“味道好奇怪”,他們說道,但臉上洋溢著微笑。
千裡之外的上海咖啡館,潛移默化影響著雲南老家的人。越來越多當地人開始注重咖啡豆品質。她還扶持老家的年輕人,送他們去學習咖啡精品化處理課程。
如今,何維琦已經物色好了在上海的第二家分店,位於膠州路,即將開業。
或許對別人而言,梧桐樹下、老房子裡的咖啡店是一種情懷,但何維琦的咖啡店,還聯系著家鄉的土地、家鄉的人。雲南的山,離上海是那麼遠,但因為一粒粒小小的豆子,它們又可以那麼近。

在上海這座城市,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都能找到各自的一方舞台,找到懂得欣賞的消費群體。
“啡嘗上海、不負熱愛”,以此為主題的2022上海咖啡文化周是城市魅力的展示,也是人與文化的情感連接。
跨越幾個世紀的光陰,咖啡與這座城市相遇、碰撞、成長,在開放、包容與創新中,傳遞城市的溫情與夢想。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