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科幻大師布拉德伯裡:登陸火星是人類未來的坦途?
如果有色人種(1949年,科幻大師雷·布拉德伯裡寫作《乾坤逆轉》時,這是對黑人的稱呼)率先登陸火星,定居下來開始新的生活,建好了城鎮,他們將如何迎接白人的到來?隨后又會發生什麼?
雷·布拉德伯裡用科幻小說的寫作來尋找答案。但寫完后,當時沒有一家美國雜志肯買下這個故事。民權運動尚未興起,冷戰已經開始,國會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正在帕內爾· 托馬斯的主持下召開聽証會,約瑟夫· 麥卡錫遲些才會登場。在這樣的氛圍中,沒有哪個編輯願意與雷·布拉德伯裡的黑人移民一起登陸火星。
上面這個故事被收錄在上海譯文社最近推出的雷·布拉德伯裡的經典短篇小說集《圖案人》中。小說集以一個全身遍布可以預知未來的文身圖案的神秘男子為線索,牽出18則“黑鏡”式天馬行空的科幻奇妙物語,每一篇都有詩意而奇詭的想象和出人意料的結局。
18個故事的關鍵詞都是“如果”:如果男人可以給自己量身定制一具機械木偶,晚上出門鬼混時留它在家打掩護,不料它真的愛上了主人之妻?如果某座沉睡的城市一夕蘇醒,啟動一切科技化感官,對人類展開瘋狂的復仇行動?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神父,在布道中卻發現真正的上帝並非如你想象的模樣?如果一群來自火星的入侵者戰戰兢兢地登陸地球,才發現人類不過是群沉迷於吃喝玩樂的蠢家伙?…
作為公認的科幻大師,布拉德伯裡的作品別具一格:並非硬核科幻,卻能洞察人性和科技間最尖銳的矛盾,抵達內心深處的欲望和恐懼。每個故事都像一則寓言,穿梭在科幻與現實、戲謔與嚴肅之間,悲觀而又不乏對人類未來最真誠的期望。
本書曾於1969年被改編為cult電影(指某種在小圈子內被支持者喜愛及推崇的電影),同名系列劇集預計將於2022年由《超感獵殺》導演邁克爾·斯特拉辛斯基搬上熒幕。
雷·布拉德伯裡1920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的沃基根,今年(2020年)是他的一百周年誕辰。自1943年開始專業寫作,他70多年的寫作生涯,激勵了數代讀者去幻想、思考和創新。他創作了數百篇短篇小說,出版近50本書,此外還寫了大量的詩歌、隨筆、戲劇、電視和電影劇本。
《華氏451》和《火星編年史》是他最為著名的作品,奠定了其科幻小說大師的地位。他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美國作家之一,“將現代科幻領入主流文學領域最重要的人物”。曾獲2000年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卓越成就獎,2004年美國國家藝術獎章和2007年普利策特別褒揚獎。
2012年6月6日,91歲高齡的布拉德伯裡病逝於洛杉磯。時任美國總統的巴拉克·奧巴馬親致悼詞:“他的敘事才華重塑了我們的文化,拓寬了我們的世界。”
《火星編年史》是確立布拉德伯裡作為一名領先潮流的科幻小說作家地址的作品。這部小說描寫了人類殖民火星的企圖,火星上的殖民化的后果,以及殖民者對於地球上的大規模核戰爭的反應。《火星編年史》既是一部社會批判小說,也是一部科幻小說,它反映了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種種焦慮和不安:核戰爭的威脅、對於簡單生活的向往、對種族主義和審查制度的反應、以及對於外在政治勢力的畏懼。《火星編年史》是一部令人贊嘆的作品,它沒有通常科幻小說不可缺少的堅硬的技術內核,卻充滿了孤獨的情感和鄉愁。貫穿全書的是夢一樣的感受。反科技的偏見、簡朴的慶典、小鎮生活的清新印象、成長過程中失落的情感以及探索未知的欲望交織在一起。正如人們稱頌他是科學幻想詩人一樣,布雷德伯裡用富於韻律和懷舊情感的優美文筆描寫幻想,其作品不僅在科幻界大受歡迎,更贏得了主流文學界的廣泛贊賞,人們將布雷德伯裡譽為文體家和意象大師,科幻界也將他稱作“艾倫·坡創始的美國幻想文學的正統繼承人”。
《華氏451度》(發表於1953)是布雷德伯裡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它進一步展現了作者非凡的才華。這部作品講述了一個以焚書為業的“消防隊員”,向一個保護書籍保擴知識的反叛者轉變的過程。故事發生在一個被極權政府統治的未來世界。極權政府取締了各類書籍報刊等出版物。蒙塔格很喜歡他的專業書籍焚燒員的工作。可是當他得知有段時間書籍是合法的、人們沒有生活在恐懼之中后,他開始質疑自己的職責。蒙塔格開始偷取那些本該焚毀的書籍,還與一位同意教育他的教授會面。當他的盜書之事被人發覺,他必須為了自己的性命而逃離。這是一部充滿象征的作品,反映了作者對現實社會的擔心。嚴格地說,《華氏451度》更像是一本哲學思想小說。
“在這個荒誕的時代,我們需要科幻。”布雷德伯裡在《圖案人》的序言中宣告自己“步履不停,隻為生命不止”。他這樣寫道:
我的侍者朋友,洛朗,在埃菲爾鐵塔附近的戰神廣場啤酒屋工作。一天晚上,在為我端上一大杯啤酒時,他向我描述了他的生活。
“我每天要干十到十二小時的活兒,有時是十四小時,”他說,“到了夜裡就去跳舞,跳啊,跳啊,一直跳到凌晨四五點鐘才上床,一覺睡到上午十點,十一點上班,再繼續工作十到十二小時,有時是十五個小時。”
“你是怎麼做到的?”我問。
“很簡單,”他回答,“睡眠如同死亡,睡著了就像死了一樣。所以我們跳舞,為的是遠離死亡。我們不想死。”
“你多大了?”我最后問他。
“二十三。”他回答。
“啊,”我感嘆著,輕輕握住他的肘彎,“啊。二十三,是嗎?”
“二十三,”他微笑著說,“你呢?”
“七十六,”我說,“我也不想死。可是我已經不再是二十三歲了。我該怎麼回答呢?我在做些什麼呢?”
“是啊,”洛朗依舊笑得天真無邪,“凌晨三點你都在做什麼?”
“寫作。”我終於答道。
“寫作!”洛朗驚愕地說,“寫作?”
“為了遠離死亡,”我說,“跟你一樣。”
“我?”
“是的,”此刻我也露出了笑容,“凌晨三點,我寫啊,寫啊,寫個不停!”
“你很幸運,”洛朗說,“你很年輕。”
“目前看來是這樣。”說罷,我飲盡杯中的啤酒,回到打字機旁完成一篇故事。(王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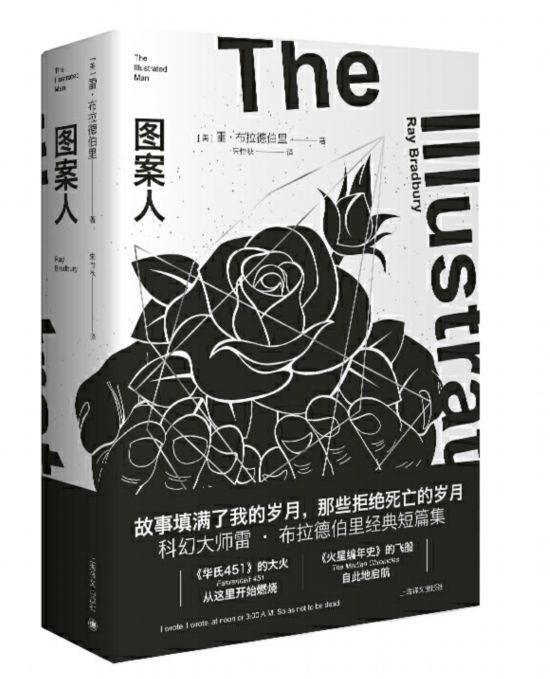
《圖案人》[美]雷·布拉德伯裡 著
宋怡秋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掃描關注上海頻道微信
掃描關注上海頻道微信
 掃描關注上海頻道微博
掃描關注上海頻道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