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昆谈北京人艺的“京味”
| 本报记者 娄 靖 |
2010年12月12日13:37
| 【字号 大 中 小】 | 打印 | 留言 | 论坛 | 网摘 | 手机点评 | 纠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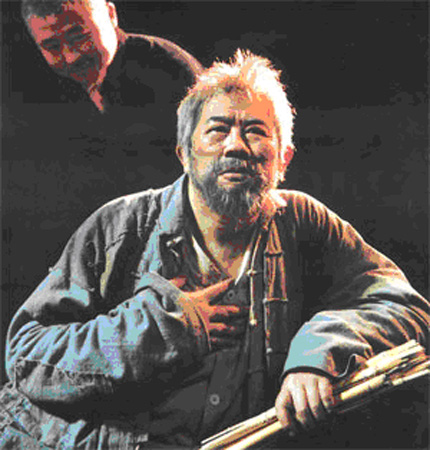 舞台上的林连昆 |
甭管什么新的流派、新的思潮,北京人艺都能将它们化为浓浓的“京味”
上海人对北京人艺特别敬重,服他们有本事把挺严肃的主题、挺洋派的东西,搞得京味十足,让北京人忍不住不能不看。前两年的《旮旯胡同》,明明是写住房解困和搬迁,却让老百姓看得特别解气、痛快。年前,他们又把一个特别荒诞的《鸟人》,即写一位洋专家给一群养鸟人搞精神分析的戏,演得京城里的男女老少都叫好,还说能从戏里找到自己的影子。竟然一连演了117场,而且是在千余人的大场子。
这回,上海的弘韵文化娱乐有限公司邀请北京人艺来上海,并让林连昆等几位演员先和记者们见见面,便有机会抓住他问个究竟。
林连昆可称得上北京人艺近10年的代表人物,他在《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盘》、《左邻右舍》、《红白喜事》等一连串的现时京派话剧中有出色的表演。看他的戏,就如坐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嚼着圆脆喝豆汁,有浓浓的土味。
问林连昆为何北京人爱看人艺的戏,他呵呵乐着,眼睛眯成一条线,和慢悠悠的京腔浑然一体。他说人艺演的都是北京四合院和市井、大杂院里普通人的生活情趣,都是些磕头碰脸遇得到的事,所以看着特别亲切。再就是戏里的掌故、一些老字号的发展、旧北京的种种故事等,知识性强,北京人特爱看,包括那些年轻人。
他说《鸟人》所以能演火,一是因为剧中的语言很有特色;二是选择了洋专家和养鸟人互相不能理解的特殊视角,这种东西方文化相冲撞的矛盾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能引起观众各自的生活联想;三是北京人爱养鸟,剧中人谈的养鸟经,让台下人听得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北京人艺以演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著称,把一个原本从西方引进的洋话剧调试得彻底地京化,《茶馆》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问林连昆,这回是如何将一个西方流行的实验性荒诞剧也能演化成现实主义的。林连昆笑了,连说问得深刻。他说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就是,甭管是什么流派、什么新思潮,他们都会归入民族话剧的轨道。他本人在演戏中把握的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什么情节,他都要在生活中找到依据。就比如他这回演《鸟人》中的三爷,从前唱京剧,现在特别的失落,住进了洋专家的精神分析康复中心后,老和洋专家过不去。林连昆说,他在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位京剧老前辈的朋友,老惦记从前京剧的辉煌,对现在的一切都看不惯。一次,他带着10个弟子去参加南方的文艺晚会,总共得了2000元报酬,可和他同台的歌星,一人就拿了4000元,还一个劲地数落招待得不好。那位老前辈气得拍桌子骂娘。林连昆就是从他身上找到了三爷心理的依据,所以演得得心应手,把观众从荒诞引入了现实。
林连昆对话剧可有太多的想法,他从《鸟人》谈到了话剧的两个走向:或是民族化,或是随西方新潮走。两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必去争谁个高低。但就北京人艺和他本人来说,更愿意奔民族化的走向,把西方的新玩艺,演化为民族化的新手段,让更多普通人喜欢并且看得懂。
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民族化,就是北京人艺的“京味”了。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上海人对北京人艺特别敬重,服他们有本事把挺严肃的主题、挺洋派的东西,搞得京味十足,让北京人忍不住不能不看。前两年的《旮旯胡同》,明明是写住房解困和搬迁,却让老百姓看得特别解气、痛快。年前,他们又把一个特别荒诞的《鸟人》,即写一位洋专家给一群养鸟人搞精神分析的戏,演得京城里的男女老少都叫好,还说能从戏里找到自己的影子。竟然一连演了117场,而且是在千余人的大场子。
这回,上海的弘韵文化娱乐有限公司邀请北京人艺来上海,并让林连昆等几位演员先和记者们见见面,便有机会抓住他问个究竟。
林连昆可称得上北京人艺近10年的代表人物,他在《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盘》、《左邻右舍》、《红白喜事》等一连串的现时京派话剧中有出色的表演。看他的戏,就如坐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嚼着圆脆喝豆汁,有浓浓的土味。
问林连昆为何北京人爱看人艺的戏,他呵呵乐着,眼睛眯成一条线,和慢悠悠的京腔浑然一体。他说人艺演的都是北京四合院和市井、大杂院里普通人的生活情趣,都是些磕头碰脸遇得到的事,所以看着特别亲切。再就是戏里的掌故、一些老字号的发展、旧北京的种种故事等,知识性强,北京人特爱看,包括那些年轻人。
他说《鸟人》所以能演火,一是因为剧中的语言很有特色;二是选择了洋专家和养鸟人互相不能理解的特殊视角,这种东西方文化相冲撞的矛盾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能引起观众各自的生活联想;三是北京人爱养鸟,剧中人谈的养鸟经,让台下人听得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北京人艺以演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著称,把一个原本从西方引进的洋话剧调试得彻底地京化,《茶馆》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问林连昆,这回是如何将一个西方流行的实验性荒诞剧也能演化成现实主义的。林连昆笑了,连说问得深刻。他说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就是,甭管是什么流派、什么新思潮,他们都会归入民族话剧的轨道。他本人在演戏中把握的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什么情节,他都要在生活中找到依据。就比如他这回演《鸟人》中的三爷,从前唱京剧,现在特别的失落,住进了洋专家的精神分析康复中心后,老和洋专家过不去。林连昆说,他在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位京剧老前辈的朋友,老惦记从前京剧的辉煌,对现在的一切都看不惯。一次,他带着10个弟子去参加南方的文艺晚会,总共得了2000元报酬,可和他同台的歌星,一人就拿了4000元,还一个劲地数落招待得不好。那位老前辈气得拍桌子骂娘。林连昆就是从他身上找到了三爷心理的依据,所以演得得心应手,把观众从荒诞引入了现实。
林连昆对话剧可有太多的想法,他从《鸟人》谈到了话剧的两个走向:或是民族化,或是随西方新潮走。两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必去争谁个高低。但就北京人艺和他本人来说,更愿意奔民族化的走向,把西方的新玩艺,演化为民族化的新手段,让更多普通人喜欢并且看得懂。
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民族化,就是北京人艺的“京味”了。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责编:励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