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丨走近科學大咖②埃默爾:不追熱點,隻盯著“沒弄明白的小問題”
10月23日下午3點半,復旦大學江灣校區生化樓報告廳,“相伯講堂”學術演講馬上開始,斯科特·埃默爾調好幻燈片,移步到演講台中央,卻沒有開口,而是后退兩步,舉起手機,對著台下的復旦師生拍了個照,“這留影很珍貴”,他笑說。

10月23日下午,復旦相伯講堂,埃默爾為該校生命科學學院師生進行學術講座。彭柏輝攝
這是美國細胞遺傳學家埃默爾在香港獲頒邵逸夫生命科學與醫學獎后,在中國再捧科學大獎——他花了40年揭示受體膜蛋白轉運與降解細胞機制,為HIV長效預防藥物來那卡帕韋的“誕生”奠定了生物學基礎,與認識了25年的老友韋斯·桑德奎斯特共同摘得2025頂科協獎“生命科學或醫學獎”。
再次來華,埃默爾欣喜不已。71歲的他面色紅潤、笑聲爽朗,那份鬆弛感讓初次見面的人很容易親近。他襯衫口袋上總別著一支鋼筆,恰如他學生所描述的,“埃默爾是一位超級自律的科學家,分分鐘都在關注科研,隨時隨地都會做筆記”。
演講中,埃默爾分享長達40年的科研馬拉鬆,每說到一個階段性成果,PPT便跳出參與的學生或合作者的照片。有一面標注“埃默爾家庭”的照片牆,展示他帶過的所有學生。他說:“科學獎項是對全體在埃默爾實驗室工作過的人的肯定,要讓他們看到自己所做研究的價值。”
科研如探險,最大的寶藏是“未知”而不是“已知”
“小時候,我喜歡通過顯微鏡來‘看’世界,這太酷了。”埃默爾生長於美國新澤西州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一家紐扣制造廠的經理。童年時,他每年都從父母那裡得到“科研裝備”作為聖誕禮物。盡管這個四個孩子的家庭並不富裕,沒上過大學的父母,還是想辦法買到埃默爾想要的顯微鏡、化學實驗套裝。“這不便宜,但他們非常慷慨。”埃默爾陷入回憶。

埃默爾接受大江東-復旦融媒體創新工作室採訪。黃曉慧攝
小埃默爾曾把一片洋蔥放在載玻片下,通過顯微鏡觀察細胞,這令他非常興奮:“細胞裡有什麼?它們如何工作?”這份好奇心,讓埃默爾在13歲時就已篤定自己對科學和數學有濃厚興趣。
中學生埃默爾因為電視節目《雅克·庫斯托的海底世界》迷戀上了海洋,於是他選擇入讀海洋學科背景深厚的羅德島大學。直至他有機會登上一艘科考船,“我發現海洋科考不像電視拍得那麼好玩,我想知道的海洋問題,也已經有了答案,但生物領域還有大量未解之謎。”
盡管如此,探索海洋的冒險精神依然深深刻在他的心裡,他把科研比作探險,“最大的寶藏是未知,而不是已知,科學的樂趣就在於你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會冒出三個新的”。
大學畢業,埃默爾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讀博。他整天要麼泡在實驗室裡研究大腸杆菌的蛋白質分泌機制,要麼抱著厚厚的期刊在圖書館裡啃,一點點摸清細菌裡蛋白質“運輸”的規律。他養成一個習慣:不追熱點,隻盯著“沒弄明白的小問題”。
在學生眼中,埃默爾對科研永葆熱情、從不倦怠。耶魯大學助理教授唐紹庚曾在埃默爾實驗室讀研,他發現,討論問題時,埃默爾經常會從小山一樣的文件堆裡,抽出某場講座的海報,指著海報背面的筆記告訴唐紹庚,這場講座的內容與他研究有怎樣的關系。
不僅隨身帶筆,埃默爾還會在床頭放一隻筆,方便他隨時夢中醒來、記錄科研靈感。“有時我甚至不開燈,在黑暗中記錄想法,第二天早上再去弄清楚我到底錄了些什麼。”說起這些,埃默爾被自己逗樂了,“我常和學生說,如果你睡覺前縈繞在腦中的最后一件事仍是實驗室項目,你就算得上是科學家了。”
這份專注、熱愛、超級自律,寫入了埃默爾的“科研基因”,並被“轉譯”為熱情洋溢的科研日常。多年來,他總是第一個到實驗室,即便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出差回來,第二天他仍會在早上6點前准時出現在實驗室。
他到底幾點來上班?一直是他實驗室的“未解之謎”——直到一次,有位研究生通宵做實驗,清晨五點半准備回家,剛出實驗室大門,就撞見埃默爾拎著包進來。
“雖然我在床邊放一個鬧鐘,但它一百天裡隻響一次,我總是在它響之前就醒了。”埃默爾笑說,“我從小就在父親的工廠裡幫忙做紐扣,早起的生物鐘也許早就形成了。”
幾十年探究,隻為弄清細胞怎麼“打掃衛生”
1980年,拿到哈佛博士學位的埃默爾,來到鼎鼎大名的蘭迪·謝克曼實驗室做博士后。當時謝克曼團隊聚焦酵母的“分泌缺陷”研究,埃默爾卻注意到一個被所有人忽略的細節:酵母細胞裡那些“沒用的蛋白質”,是怎麼被運到溶酶體這個“垃圾站”裡降解的?
在謝克曼鼓勵下,埃默爾開啟一段長達20年的探尋之旅。
起初,研究並不順利。“那時候,還沒有人類基因組測序,沒有基因編輯技術,細胞遺傳學研究好像在黑箱中摸索。”唐紹庚說。
為走出黑箱,埃默爾和團隊花費數年,用基因融合技術這一傳統遺傳學手段篩選出33種“垃圾運輸出問題”的酵母突變體,還給控制這些功能的基因起了個名字叫“VPS 基因”。最終,他們與其他實驗室共同確認了40多個和“細胞垃圾清運”相關的基因。
當時沒人知道這些基因到底有什麼用,埃默爾覺得,弄明白細胞怎麼“打掃衛生”,肯定很重要。直到 1998年,他終於揭開了細胞“垃圾清運系統”的核心——一種叫 ESCRT的蛋白質復合體。
如果把細胞比作一座城市,ESCRT 就像穿梭在街道上的“垃圾車”:它們能識別貼有“廢棄標簽”的蛋白質,把這些“垃圾蛋白質”打包好,精准運到溶酶體裡“粉碎回收”。更神奇的是,這套系統不僅負責“扔垃圾”,還能參與細胞分裂、修復細胞膜,甚至影響神經元的生長,一旦它出故障,就可能引發癌症、帕金森病等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 HIV 在內的許多病毒,會劫持ESCRT機制以離開受感染的宿主細胞。
“酵母液泡相當於哺乳動物的溶酶體,能夠展示人類細胞中發生的事情。”在埃默爾的描述中,細胞的世界充滿無窮樂趣,上演著一出出驚心動魄的“大戲”。他把自己的核心研究,比作在酵母細胞這個“微觀工廠”裡抓出了一群關鍵“交通調度員”——ESCRT復合體,這就像一把萬能鑰匙,打開了理解細胞膜重組、病毒傳播等多個關鍵過程的大門。在此基礎上,桑德奎斯特教授后續發現了ESCRT復合體在HIV病毒逃逸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藥企根據埃默爾和桑德奎斯特的發現研發出HIV長效免疫針劑,有望改變全球艾滋病流行態勢。兩人的成就,完美詮釋了基礎科學研究如何通過揭示生命機制,最終轉化為具有全球健康影響力的實際應用,堪稱科學造福人類的典范。”2025頂科協獎“生命科學或醫學獎”遴選委員會主席蘭迪·謝克曼這樣評價。
他的辦公室大門永遠向學生敞開
“抱歉,我今天不應該用英文回答你們,隻可惜我的中文還不夠好。”復旦大學相伯講堂的演講進入問答環節,遇到學生提問的英文不大流利時,埃默爾耐心傾聽,還由衷致歉。
在康奈爾大學,他對學生好是出了名的。“學生是科研給我的寶貴財富,我有責任帶領他們做好研究,這讓我很有成就感。”埃默爾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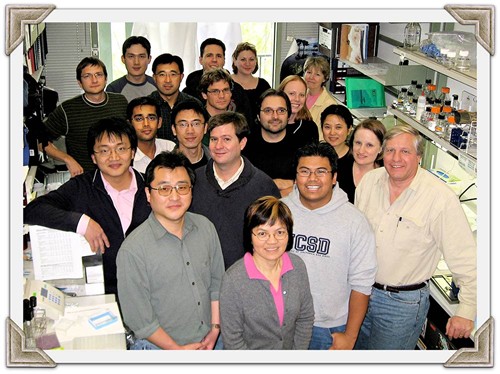
埃默爾(右一)和學生們在實驗室。資料圖片

埃默爾(后排)與學生們。資料圖片
埃姆爾指導過加州理工學院、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和康奈爾大學30多名研究生和50多名博士后,可謂“桃李滿天下”。
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李明曾是埃默爾的博士后。博士后面試時,埃默爾年近花甲,時任康奈爾大學生物化學、分子和細胞生物學研究生院院長,每天會議一個接著一個。但他步履飛快,帶著李明走遍研究所的四層樓,嘴裡念叨著“這個房間有好儀器”“這個房間是誰,在做什麼研究”,李明一路小跑才能跟上。“談到科學,他就激動。從前面試一位學生,他聊著聊著,眉飛色舞,幾乎要從椅子上跳出來。”李明說。
對待科研,埃默爾既充滿熱情,又十分嚴謹。說起實驗室制作培養基培養菌落的場景,唐紹庚仍歷歷在目,“他問得特別細:你是怎麼挑菌落的?挑取時用的是什麼牙簽?培養基配方是什麼?濃度多少?體積多少?培養溫度是 26 度還是 30 度?幾乎每個細節都問到了。”
埃默爾的中國研究生凌亞鼎說:“他一直給我正向的反饋,讓我不要對研究失去信心。”凌亞鼎本科學化學,初進實驗室時幾乎沒有生物學基礎,但埃默爾看重他的好奇心和學習能力。初次見面,埃默爾就從書櫃裡拿出一本1500多頁的《細胞的分子生物學》遞給凌亞鼎:“有空時看看,補充專業知識。”

埃默爾(左二)與學生凌亞鼎(左一)在2025頂科論壇上合照。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供圖
“他總是鼓勵學生大膽探索,有一點小進展,他就會說‘great(很棒)’wonderful(非常好)。”凌亞鼎說。
有一次,一個難以合成的蛋白結晶終於出現在唐紹庚的顯微鏡下,他立刻沖進埃默爾辦公室,把他拽到實驗室,讓他透過鏡頭親眼看看這一發現。即便埃默爾並不熟悉這一領域,也難掩興奮,當即找來系裡研究蛋白結晶的教授開會,一起討論新發現。
“他是一個很顧家的人,多年前,他就和家人約定,每天都會陪家人吃晚餐”。埃默爾的妻子主修音樂和早期教育,是一名教師。“她養育了我們的孩子並幫助他們成長。”談及家人,埃默爾嘴角上揚。

2025頂科論壇現場,埃默爾和夫人合影。採訪對象供圖
事實上,埃默爾只能擠出時間陪伴家人,因為他實在太愛科研。“她確實有時會沮喪,因為我會花大量的時間在實驗室。但她尊重我,愛我,她愛我們的家。”埃默爾說,他承諾過妻子70歲就退休,但一年過去了,這個承諾尚未兌現,他還沒有完全離開實驗室,隻不過他現在到實驗室不是早上五點半了,而是六點多。
“我也能睡懶覺了,哈,太棒了,雖然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仍然很早。”埃默爾笑著說。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